
河南大学原历史系主任、教授,河南大学出版社首任总编辑朱绍侯先生
96岁高龄的恩师朱绍侯先生于2022年7月23日下午驾鹤西去,闻知此讯,不胜悲痛,心潮起伏,彻夜难眠。回忆四十多年来,不论是做先生的学生,还是做先生的麾下,都能时时得到先生的耳提面命,谆谆教诲,使我受益终生,没齿不忘,谨以此文,寄托哀思,悼念先生。
相 识
我认识朱先生是在进入河南大学(开封师范学院)历史系读书之后。我们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学生,给我们授课的都是系里最好的老师。那时“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老师们靠边站了十年,一朝有机会重上讲台,真是焕发了革命青春,想尽办法,使出浑身解数上好课。朱先生是历史系副系主任,因为工作比较忙,没有给我们开通史课,只给我们开设了“秦汉土地制度”讲座。朱先生是东北沈阳人,高高的身材,方方的脸庞,浓眉大眼,不苟言笑,操着一口纯正的东北话,给人一种不怒而威的感觉。
1980年,学校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给教授盖起了连体别墅,俗称“教授楼”,是当时学校最好的房子。由于朱先生学术成果丰硕,是“文革”后历史系破格提升的最年轻的正教授之一,所以,按照政策就搬进了这个院子。我们家和朱先生家是前后排,隔路相望,可我从未和他讲过话。一是我对先生有一种敬畏感,不敢和他说话;二是觉得我们年级一百多号学生,朱先生可能不认识我。
这年初冬的一天夜里,一场纷纷扬扬的大雪,把整个世界银装素裹。我早上起来拿着扫帚在路上扫雪,突然,一个浑厚的男中音在我身后响起:“小敏,你的毕业论文由我指导。”我吃了一惊,急忙回过身来,啊,是朱先生!我一时语塞,不知怎么回答先生的话,只是“哦哦”两声。朱先生微笑着从我身边匆匆走过,我的心里却翻江倒海,不是滋味。朱先生认识我,还知道我的名字!我却从没主动和老师讲过话,这可是大不敬啊!
为了写好毕业论文,我真是下了一番工夫。猫在图书馆查材料,列大纲,写初稿,反复修改,折腾了几个月,眼看到了交稿时间,却迟迟不敢呈送先生审阅。但是,丑媳妇终究要见公婆,实在不能再拖下去了,我才在一天傍晚,硬着头皮把稿子送到朱先生家。谁知第二天晚上,朱先生就拿着论文到我们家来了。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儿,心想肯定是不合格被打回来了。我忐忑不安地请朱先生落座,眼睛盯着他手里的论文。朱先生看出了我的心思,笑着把我的论文夸奖了几句,然后拿出一份刚出版的考古杂志,让我把新发现的描写汉代杂技表演的画像石的考古资料用在论文里。听着先生的指教,我心里不由得升腾起对先生治学的严谨、扎实,眼光的敏锐、高远,工作的务实、高效由衷的敬仰。在先生的悉心指导下,我的论文忝列优等。
提 携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二十五中教书。1985年春的一天,朱先生来到我们家,问我愿不愿意回到河大出版社工作。我一听喜出望外,连声答应愿意。因为这时我们家上有八十多岁的外祖父,下有一岁多的儿子,这一老一小都需要照顾,能回母校工作,临近照顾家中的老人和孩子,是我梦寐以求的事。在朱先生的帮助下,没过多久,我就调回了学校,在朱先生任总编辑的出版社工作,由此开始了与先生的不解之缘。
记得刚到出版社时,社里连领导只有8个员工。我们什么活都干,参加校对稿子、负责邮购书款的领取以及管理资料室的书报等。一年以后,人员增多,朱先生把我调入文史编辑室做编辑工作。从此,我走上了专业人员的道路。
朱先生安排我做的第一本书是《唐代士大夫与佛教》,是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的郭绍林先生的硕士论文。作者八易其稿才交给我们出版。那时候都是手写稿,整个文稿字迹清楚,娟秀,无一处涂改,可谓齐、清、定。更难能可贵的是,作者还把容易混淆的字都在旁边标出,以提醒编校排版人员注意。这部书稿我认真地审读了两遍,并核对了引文,竟然挑不出什么毛病,实属上乘之作。这是朱老师为照顾我这个初出茅庐的小编辑而特意安排的。随着时光的流逝,工作上的接触越来越多,对朱先生由陌生而熟悉,而敬仰,而爱戴。朱先生的言传身教,耳提面命,使我在工作中如坐春风,如沐春雨,慢慢地成长起来。
朱先生审稿从来不用红笔改稿子,都是用铅笔。他常说,作者对于编辑来说永远都是专家,编辑改稿子用铅笔,如果改错了可以随时擦掉,如用红笔,改错了不易更改,把作者的稿子画的满篇皆红,作者会不乐意,也有不尊重作者劳动之嫌。
1993年春,我的一位在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长期从事中国思想文化研究的同学李振宏萌生了编写一套“元典文化”丛书(30本)的设想。当他把他的想法跟我谈了之后,凭着编辑的敏感使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义、很有价值、市场上尚缺的选题。于是就邀请他和我一起向管金麟总编(那时朱先生已退居二线)作了汇报。管总编听后非常认同,让我们起草选题策划报告,提交社里讨论。我们又一起请教了朱先生,先生对这个选题大为赞赏,并就丛书的规模提出了一些建设性意见。在社里的选题论证会上,朱先生就此选题的价值、意义、出版规模做了鞭辟入里的讲述,使选题顺利通过论证,并被省局列为重点选题。为了这套丛书能够按计划出版,朱先生不顾教学和科研工作繁忙,还主动承担了部分书稿的责编和终审任务。
1995年6月,在出版社成立10周年即将到来之际,丛书第一批10本问世了。由于丛书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有积极的意义和价值,所以一经出版,就受到《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出版》等多家报刊的高度重视,相继发表书评、书讯20余篇,一致认为丛书“旨趣高远,而行文切实,为一雅俗共赏佳品。”《光明日报》“史林”版还以丛书为依托,开辟了“传统文化经典笔谈”专栏,进行了为期3个月,延续14期的专题讨论。为了扩大丛书的影响,1996年5月7日,出版社又与光明日报社理论部联合在京举办了“中华经典与现代文化建设”学术讨论会,朱先生和张岱年、季羡林、戴逸、何兹全等著名学者一起参加了会议。此次学术讨论会在学术界、文化界、出版界产生广泛影响。丛书曾一举获得了“第十届中国图书奖”、河南省“五个一工程”奖和河南省“优秀图书一等奖”等奖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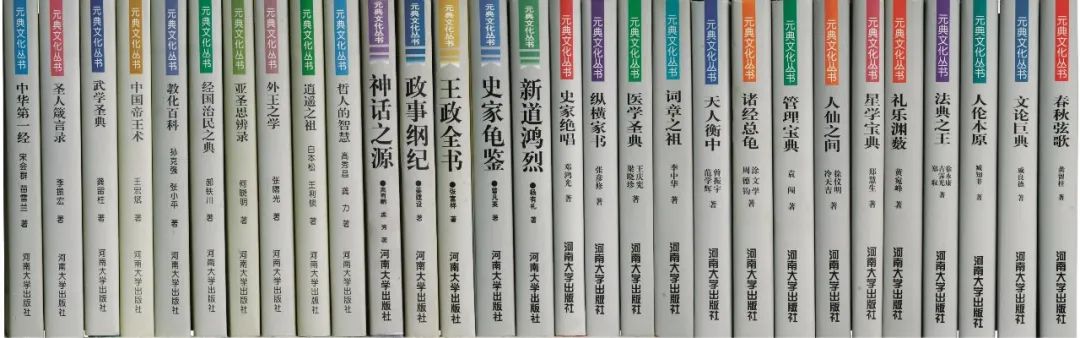
“元典文化”丛书
河南大学出版社
1995年,是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1994年初,我想策划一套适合广大青少年阅读的、描写抗日战争中中国人民英勇抗击日寇的著名战事的纪实丛书,以弘扬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当时,有同志认为我是在“赶热闹”,让我很是踌躇不决。这时,又是朱先生高瞻远瞩,审时度势,果断地肯定了我的策划报告,坚定了我做下去的信心,他还在百忙中抽出时间和我一起参加编写会议,帮我把握方向,调整作者思路,解决写作中出现的问题,有时与作者沟通商榷直到晚上八九点钟,错过了吃晚饭时间,而朱先生始终不急不躁,耐心与作者商量,最终和作者达成了共识。他还挤出时间终审书稿,使丛书的编辑出版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丛书出版后,受到省委领导和省委宣传部的高度重视。一位省领导同志曾在省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中介绍我省有关抗日战争图书出版情况时,重点介绍了这套丛书,时任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的葛纪谦同志还为丛书写了序言。《河南日报》《河南新闻出版报》《民国档案》《东南文化》等报刊也相继发表了书评、书讯,称丛书是一套“实施爱国主义教育的好教材”。丛书也由此获得省“五个一工程”奖和省优秀图书二等奖。可以说,没有朱先生的鼎力相助,就没有这套丛书的问世。
大学出版社承担着为高校教学和科研服务的重任。为了满足教学需要,出版社决定邀请著名专家学者组织编写一套高校中国史通史教材。拟请华中师大的章开沅先生领衔主编《中国近代史》教材,请朱先生挂帅组织编写《中国古代史》教材。朱先生虽然主编过一套颇受欢迎、连年重印的十院校本《中国古代史》,是几十年来历史学界公认最成功的高校文科教材,但为了方便教学、为了出版社的出版计划,他还是从大局出发,不顾年近耄耋,毅然承接了编写任务,和我们一起北上长春、北京,南下广州、韶关,召开编写会议,拟定编写大纲,分配编写任务,实地解决编写中的问题,最终按时高质量的完成了编写任务,有力地支持了出版社的工作。这套《中国古代史教程》抛弃社会形态概念体系,摒弃阶级斗争思维,用本土语言叙述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是一个可喜的尝试,对今后的中国古代史教材编写将会产生重要的示范性效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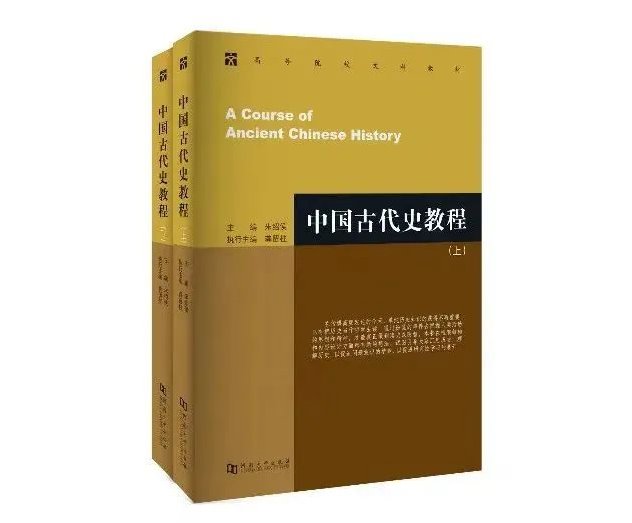
《中国古代史教程》
河南大学出版社
朱先生不仅仅是对自己的学生尽力帮助、提携,对所有的同志也都是如此。众所周知,职称评定是对专业技术人员业务水平和工作能力的一种评判和认可,也是专业技术人员努力追求的目标。因评审条件时有变化,我们出版社的一位老同志行将退休,尚未晋升正高职称。就在评审日期临近之时,他突然决定退出申报。听到这个消息,朱先生很是着急,他不愿看到这位条件具备的老同志辛辛苦苦工作一辈子就这样错失良机。他约同社长赵帆声先生一起来到这位老同志家,苦口婆心的分析劝导。看到这两位年近七十的老领导,不顾天黑路滑,冒雨前来劝说,这位老同志感激之情无以言表,同意继续申报。就在这次申报后,他如愿以偿,顺利晋升正高职称。
教 诲
孔子曰:“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有何于我哉?”朱先生不仅自己勤奋治学,硕果累累,为后学的榜样。他还不遗余力的谆谆教诲身边的每一个人,这使我受益多多。
那是“元典文化”丛书刚刚启动阶段,有的同志对做这样的大型套书心存疑虑,唯恐投入大而收益小,造成亏损。当我听到议论后,心中也很纠结,觉得社里盈利非常艰难,如果此书造成亏损,挺对不起大家的,因此就想打退堂鼓。朱先生看出了我的心思,语重心长地告诫我说:“任劳任怨大家都知道,也都能做到任劳,但是任怨做起来就比较难了。你工作不怕任劳,但也要学会任怨啊!”朱先生的话消除了我的困惑,坚定了我出好书的信心,于是排除杂念,全心全意地投入到丛书的编辑出版工作中。功夫不负有心人,几经寒暑,终于修成了正果。
从此以后,我牢记朱先生的教诲,秉承着任劳还要任怨的信念去做事,去做人。真是“经师易获,人师难得”,先生的金玉良言,让我终生难忘。
还有一次,一位同志出差因派车的事与办公室负责此事的同志发生了口角,后来社长知道了此事,亲自为该同志派了车。但那位同志却赌气不出差了。当我把此事告诉朱先生时,他微笑着说:“你转告那位同志,不要得理不让人。社长已给你派车了,就应该去,要懂得得理也要让人。”当我把先生的话转述给那位同志后,那位同志很愧疚,连声说:“朱先生说得对,朱先生说得对!”朱先生的这些话,虽然并不深奥,但却道出了同志之间要团结共事、谦和礼让的做人道理,也是先生为人处世大度为怀、宽厚待人的真实写照,我一直将它铭记在心。
我的毕业论文是朱先生指导的,他还鼓励我投出去发表。大学毕业后,我就试着投了出去,还真被《历史知识》采用了。当我把这个消息告诉朱先生时,他笑眯眯地说:“很好!我让其他几位同学将文章投出去,也都发表了。”先生那副欣慰的表情,比他自己发表了文章还要高兴。从那以后,处于对朱先生的敬仰和信赖,我每写一篇文章,都要拿给朱先生请他“初审”,听他提意见。他不管多忙,都是欣然应诺,而且很快就审阅完毕,立马把意见反馈给我。他的意见都是高屋建瓴,一针见血,让我非常受益。以后,为了心中有底,没有经过朱先生过目并且认可的文章,我就不敢拿给别人看或者是去投稿。
另外,我在工作中遇到什么难以释怀的事情或者有解不开的疙瘩,也爱跑去向朱先生唠叨唠叨,诉说一番。朱先生总是放下手头正在做的事情,耐心地听我讲述,然后客观地进行分析,理智地做出判断,热心地给予指点。有时仅短短的几句话,犹如醍醐灌顶,顿时让我茅塞顿开,心里豁然开朗。可以说,我取得的每一点成绩,都有先生付出汗水和心血;我前进的每一步,都有先生的扶持和教诲,先生就是我的人生导师。
振宏在朱先生九十华诞纪念文集的序言中深情地说:“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作为先生的弟子,十年间,我们差不多就是以这样的心情,陪伴着先生走过来的。”这样的心情我也体会颇深。我觉得,从九十岁以后,朱先生一直在努力地爬坡,一是在爬年龄的坡,一是在爬学术研究的坡。他勇敢地越过一道又一道障碍,不断地在与年龄竞争,不断地在超越自己,实在是不容易!我们期盼着为先生举办期颐之年的庆典。但是,没有想到,先生在96岁高龄时离我们而去,令人万般不舍。振宏在挽联中写道:“读书教书著书与书结缘书生天性,做人诲人度人与人为善真人慧根。”这是对先生一生的真实客观的写照。愿先生的精神发扬光大,泽被后世!

